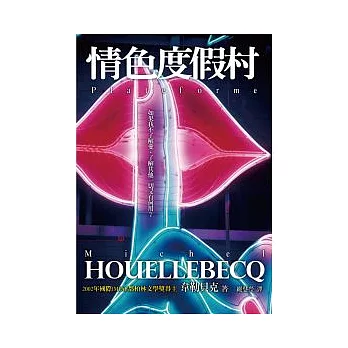台北藝術節《烏布王》(Ubu
and the Truth Commission)
時間:2014.08.16 19:30
地點:台北中山堂
原著:Alfred Jarry
原著:Alfred Jarry
戲劇與學術顧問:Jane Taylor
製作:翻筋斗偶劇團 Handspring Puppet Company 更多劇照
原來,不僅政客會將敵人妖魔化運用,我們不自覺也會在內心中將暴君予以妖魔化,以為他們如何異於常人泯滅人性……。然暴虐者往往並不面目可憎,甚至可能外表溫良可愛、內心荏弱可憐、動機幼稚滑稽、視界平庸無奇,與他們造成的巨大災難完全不能匹配。這點《烏布王與真相委員會》在形象的塑造上,無疑超越了時空和地域,隱喻了全世界的壓迫與不幸。
本劇改編自十九世紀法國作家賈里(Alfred Jarry)的知名少作《烏布王》(Ubu Roi)——1888年,還是十五歲少年的賈里,為諷刺學校老師而謔寫的偶戲劇本,八年後在巴黎正式演出,結果引起劇院暴動;其屎臭橫流的粗口和暴虐反常的角色,打破了現實與幻想的藩籬而成為超現實主義和荒謬戲劇的運動先驅。英文劇名Ubu and the Truth Commission(或譯作「烏布與真相委員會」)比較準確地點出本齣戲的改編所在:架構在南非政府1995年組成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簡稱TRC)的紀實素材上的鬧劇,從奇幻荒謬猶帶諧趣的形式中尋求人心如何面對暴力真相。
賈里筆下「烏布王」脫胎自莎士比亞之一知名悲劇主角馬克白,是個註定有君王命而無君王才的人,愚蠢、懦弱、貪婪、殘忍,毫無同理心且剛愎自用,受妻子「烏布媽」唆使而登基為波蘭王,立刻變成心狠手辣的暴君。十九世紀的波蘭,為俄、普、奧三鄰國瓜分,是個在歐洲地圖上不存在的國名——國不成國,君不似君,因而成為荒謬滋生的沃壤。人擺錯了位置,本是一件可悲的荒謬,賈里強化了荒謬乖離的成分而覆蓋了人文主義的悲壯情懷。
動畫家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烏布王與真相委員會》,讓烏布王降落於上世紀末的南非共和國,成為三十餘年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的加害者的總體化身,其形象是穿著白色內衣的白人國王,其談吐是愚蠢刻薄卻文雅矯飾;他的妻子是穿著粉紅色誇張睡袍的黑人王后,爆粗口粉碎烏布王的虛矯,懷疑烏布王的鬼祟行蹤,最後發現他原來忙著在銷燬過去屠殺人民的證據之後,然竟無知地稱頌丈夫「避免我們遭受『危險份子』侵擾」,毫不覺歷史被竄改和遺忘的可恨。真人演員,圍繞以充滿諧趣與奇想的動畫和造型物偶,這種真實與虛構的強烈反差,造成另一種難以言喻的荒謬感。
但瘋狂鬧劇如何演繹冷酷的紀實真相?而笑謔過後如何面對依舊楚痛的記憶?是本劇帶給我們最艱困的省思。而藝術家如何在真實與虛構、創傷與戲謔中取得藝術倫理的平衡,頗值得我們借鏡,也是我特別想探討的重點。
政治學者吳叡人曾歸納近代史上對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進行清算處理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工程有三種模式:紐倫堡大審式的「報復」,西班牙對佛朗哥獨裁的「遺忘」,南非TRC創造的則是第三種模式:追究歷史真相的重點不在於追懲白人政權的惡行劣跡,而追求奠基於真相的和解。故以加害者承認犯行以換取有條件的赦免,讓受害人透過真相的陳述,得以撫平創傷;透過寬恕,得以突破痛苦的禁錮,而加害者透過罪行真相的交代和懺悔,得以洗濯他們的罪惡。從而促成社會和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彩虹之國的和解與重建之路》中譯本導讀)
這齣戲創作於1997年,距離1995年11月29日南非政府宣布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不到兩年。壓抑三十餘年的真相在十八個月內驟然釋放,產生無比藝術創作能量。根據導演肯特里奇描述:TRC走訪各鄉鎮舉辦聽證會,在一間間地方教會與學校禮堂,設置一模一樣的場景:一張桌子與委員會人員的桌子同高,讓證人們不需抬頭仰望他們的桌子,兩或三間給口譯員的玻璃室,還有掛在委員們身後寫著「和解帶來真相」的大旗幟,證人用半小時的時間說著他們的故事,「他們停頓、哭泣、偶有坐在他們身邊的專業安慰人員趨前安撫他們的情緒」,這些畫面經由電視或廣播播送,「簡直就是個公民劇場,在公開聽證會上說著個人的悲痛,被吸收進入眾人的身體政治中」。(見藝術節官網〈鱷魚的嘴巴──《烏布王》導演的話〉)
劇作家珍.泰勒(Jane Taylor)更從1987年起就在南非各地緊急記錄過去十年種族隔離的攝影、圖片、文獻,從事搶救歷史紀錄的工作。1996年她舉辦「斷層線」系列文化活動,包括展覽、論壇、廣播、社區藝術行動和工作坊,邀請各國作家朗誦有關罪行、補償、記憶、哀慟的相關詩作;也曾以卓別林《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為例,和學生激烈辯論:「我們究竟能不能藉由鬧劇形式來討論人權霸凌議題?」(見藝術節官網〈編劇的話〉)。由這些紀錄可見藝術者在創作倫理與人道倫理之間的紆衡。導演肯特里奇對本劇的定位是:「試著要解釋這些回憶,並非要重現回憶本身。」
身為知名動畫家的導演,從《烏布王》原作者賈里的手稿造形出發,呈現一種奇想謬思的諧趣,黑白碳筆的粗獷線條,除呼應執頭偶的木刻質感,也與演員的風格化的肢體動作線條構成美麗的視覺合奏。禿鷹、鱷魚、三頭狗等戲偶,巧妙融合日常物件,宛如一個個奇異的隱喻,加入這場以戲謔為名恣溢瘋狂想像力的遊戲。到了後半段聽證會時,證人偶採類寫實造形(細緻的偶頭木工在觀眾席後方無法看清楚有點可惜),動畫配合證詞,將其敘述畫面做風格化再現,陡然擔負一部分事件的示意功能。真相的沈重與鬧劇的輕佻在這裡無法同步,似乎顯出集體記憶從重現到解釋的艱難,猶如真相從理解到和解之路的漫長。
TRC主席圖屠主教(Desmond Mpilo Tutu)說:「我們不能隨口說說,並說過去的總會過去,因為他們不會過去並持續困擾著我們。真正的和解是代價高昂的寬恕,永遠不會便宜。你不能原諒你不知道的事情。」(We cannot be facile and say bygones will be bygones, because they
will not be bygones and will return to haunt us. True reconciliation is never
cheap, for it is based on forgiveness which is costly. You cannot forgive what
you do not know)
社會重獲真實記憶,是轉型正義的要件,也是真正和解的起點。這個改編版的《烏布王》對轉型正義尚未完整的台灣觀眾來說——轉型正義包括三個環節:對受害者的賠償、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上的追訴、對真相的發掘。台灣民主化雖逾二十年,對「轉型正義」之處理其實還停留在補償受害者的層次,故還有「民間真相和解與促進會」以民間力量在繼續努力、25年後鄭南榕仍被污名為「恐怖分子」、歷史教科書在爭議中硬是被「微調」等事件,並且由於族群記憶無法整合而被政客操作簡化為藍綠對決,類似問題仍將不斷發生——於是看完《烏布王》後,我並不覺得這是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遙遠寓言,而是齣令人如梗在喉無法暢笑的現實鬧劇。